文 / 管中閔
「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 \\ 黃昏裡掛起一盞燈」(鄭愁予,野店)
在坑道的夜晚,留在辦公室看電視的人離開後,和我同住的文書兵很快也會就寢,之後辦公室就屬於我一個人。四百多個夜晚,一燈獨坐,除了讀書和聽音樂,還能再做些什麼?當然就是寫詩啊!
我從高中時開始讀現代詩,原先不太能體會,後來看得多了,慢慢看出其中味道,從此非常著迷。看到別人寫得好,就覺得自己也來得,於是摸索著寫。大學時能讓我放棄麻將而留在山上的事,就是聽華岡詩社辦的演講。當時詩社的 #向陽 和 #劉克襄 等人很熱情,會特別招呼參加的新人。然而讀詩和寫詩,是我生活中自得其樂,只屬於自己的一個秘密,我幾乎沒有告訴任何人;以前的同學們不知道,後來軍中同袍們也不知道。寫詩多從情詩開始,所以一定要有寄情的對象。我十六歲認識的那位女孩,我大一時她家移民海外,我將所有的想念都寫在一封封信裡與一首首詩裡,飄洋過海送到她手上。不料這些信和詩如今竟然成為她(現已是老太太)威脅我的把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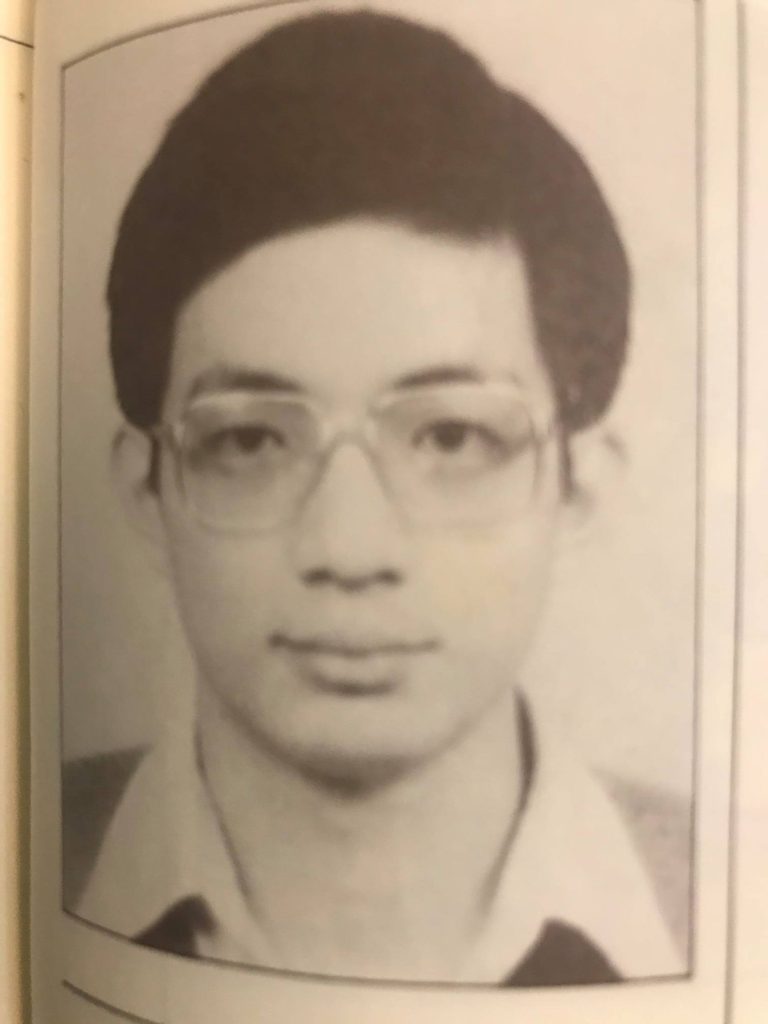
大約春夏之交,我看報時注意到第二屆時報文學獎開始徵稿,而且新增了敘事詩獎,我立刻心動,躍躍欲試。1979 年適逢五四運動一甲子,報章雜誌有許多文章討論這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,中國時報還出了一套書。我很認真的讀相關文章和歷史記載,情緒也都沈浸在那個動盪的時代裡,所以很自然的選擇「五四運動」作為敘事詩主題。不過我不曾料到四十年後,五四運動一百週年時,臺灣媒體與文化界對這段歷史已幾近冷漠。
題目雖定,但我幾次提筆,總是寫了幾行就頹然放棄,因為無法寫出自己的感覺。一直拖到截稿日前,我知道如果趕不上這班船期,就肯定會錯過這次徵稿。開船前一晚我再次動筆,從晚上十點到早上五點多,幾乎是一氣呵成的寫完,重新謄寫後託人帶回臺灣寄出。那一天是 1979 年 8 月 24 日。

我的題目「日月不淹春秋序」,取自離騷:日月忽其不淹兮,春與秋其代序。我從五四的歷史與社會背景出發,寫巴黎和會的掙扎,五四遊行的情緒,到火燒趙家樓的高潮,最後以自己的感想做結。全詩 240 行,分為十節,每節均以詩經的兩句作為小標題:
一, 棠棠者華,其葉湑兮(小雅,北山之什) 二, 正月繁霜,我心憂傷(小雅,祈父之什) 三, 泂酌彼行潦,挹彼注茲(大雅,生民之什) 四, 漸漸之石,維其高矣(小雅,都人士之什) 五, 倬彼雲漢,昭回于天(大雅,蕩之什) 六, 鼓鍾將將,淮水湯湯(小雅,北山之什) 七, 龍旗陽陽,和鈴央央(周頌,臣工之什) 八, 王旅嘽嘽,如飛如翰(大雅,蕩之什) 九, 經始靈台,經之營之(大雅,文王之什) 十, 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(小雅,桑扈之什)
這是四十一年前的舊作,現在重看,文字難入方家法眼,我就不摘錄其中內容,以免有瀆大家清神。 幾個月後,當我幾乎忘掉這件事,突然收到中國時報通知我得到敘事詩獎的佳作。看到來信的剎那,我非常興奮,但隨後又有點失落,覺得「佳作」有點像安慰獎。不過幾年後我慢慢認識到,自己寫詩的才情也僅止於此了。一個意外的收穫是,指揮部居然放了我一航次的假,讓我回臺領獎;這是後話了。
1980 年代中,我在 UC San Diego 念書時認識了葉維廉和鄭樹森兩位先生(他們系正好在經濟系旁邊),也和鄭樹森先生逐漸變成好朋友(我後來稱他鄭公)。鄭公學識淵博極了,是 UCSD 公認的 walking encyclopedia。有一次我提到得獎的舊事,鄭公說:難怪初認識時覺得你名字有點眼熟。原來葉先生和鄭公都是那次敘事詩獎的評審,而鄭公說他評我的作品為第一名;他後來將手寫的評審意見影印一份給我,我還保存著。我才情有限,竟然曾被比較文學的大師評過第一名,這個寫詩生涯也是值了。
(照片第一張我自己都沒有,是翻拍自檔案照片,另一張翻拍自「五四與中國」一書。)
(未完待續)














